数码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本文感谢易舒对《Rijksstudio: Make Your Own Masterpiece!》一文的翻译。
光韵的衰竭……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大有关,即现代大众具有着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就像他们具有着接受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的强烈倾向一样。[Benjamin, 1936]1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机械复制时代中,Walter Benjamin(瓦尔特·本雅明)如是说。数码复制时代中,光韵2又何以重塑?
Rijksmuseum(国家博物馆)位于阿姆斯特丹,主馆经大幅改建后在今年四月重新开放。若留意过我们三月间的报道,或许会对其全新的文字标志还存有些许印象。配上新的标语“国家博物馆,尼德兰淄博物馆”(Rijksmuseum, the Museum of the Netherlands.),该馆一改三十二年的旧牌匾,尝试打造一个简单清晰的国际化形象,传递平易近人的情感讯息。
在品牌更替之际,Rijksmuseum 也重新思考了数码复制时代中艺术作品的展示方式及艺术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官方网站推翻了自二〇〇四年以来的陈旧框架,于去年十月末上线了全新版本。此番网站改版增设了一个特别的项目:Rijksstudio(国家博物馆工作室)。在 MW2013 上,Rijksmuseum 数码主管 Peter Gorgels 专门发表论文加以介绍3。借此,我们得以深入窥探 Rijksstudio 的设计细节及博物馆幕后的策划理念。
原真性的挪移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艺术品的机械复制品所处的状况可能不太会触及艺术品的存在——但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Benjamin, 1936]4
有别于传统博物馆的官方网站,Rijksstudio 这个 web app 的主旨之一是开放高品质的图像。十二万五千幅艺术作品经过数码化后,可通过互联网自由访问。以 300 dpi 转制的高清图片,边长尺寸高达 2500 像素;不但没有水印,而且均可免费使用,没有版权限制。
今日的互联网世界已成图片海。然而,传统博物馆仅仅将网站作为一个线上数据库,发布的大多是艺术作品的缩略图,伴随提供的却是大篇百科式的说明信息。另一方面,主宰互联网的几大服务中,信息检索、知识共享及社交互动的平台已相当成熟,例如 Google、Wikipedia、Facebook 和 Twitter。它们不但功能精专,而且对外开放了丰富的 API。
面对此种数码景观,Rijksmuseum 在网站项目中专注于陈列来自博物馆自身的、真正含有附加价值的信息。同时,在信息展示的层级设计、内容的筛选和重组等方面,也做了一些领先的尝试:在线作品的默认视图可能不是全幅的缩略图,而采用某个预先框定的局部;砍掉了大量的作品描述文本或数据信息,而将这部分职责转交给 Wikipedia 等第三方资料库。博物馆的互联网平台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数据库,而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展示媒介。通过对展品相关的图文取舍,网站编辑充分体现了自身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及策展思想。另外,在某些非展品相关的页面中——比如“地址及路线信息”页面的下方——还加入了一些作品特辑。彩蛋式的编辑手法,也凸显了博物馆的在线策展趣味。
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可以用一张照相底片复制大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Benjamin, 1936]5
Gorgels 在论文中提及 Flipboard 和 The Guardian Eyewitness 两枚 app,并对它们在平板设备上的内容呈现及交互方式给予了肯定。不难看出,Rijksstudio 的策划者对原图(original image)有着格外的执着。无论是技术性的图像分辨率,抑或在界面设计中直接强调“图像本身”和“与原图进行交互”的重要性,都反映出了一种对 Benjamin 原真性概念的挪移:一种从原作(original artwork)到原图的置换。然而 Gorgels 在论文结尾处对光韵进行讨论时,复制品与原作的界限又再次明晰起来。
触模式交互和“接近”的隐喻艺术创造发端于为膜拜服务的创造物。……正式这种膜拜价值在今天变得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有些神像只有庙宇中的神职人员才能接近,而有些圣母像几乎全年被遮盖着,中世纪大教堂中的有些雕像就无法为地上的观赏者所见。[Benjamin, 1936]6
除了高品质的图像,Rijksstudio 另有两大主旨:与公众互动;以及“接近”(closeness)。后者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被提出。

荷兰著名书籍设计师 Irma Boom 用大巧不工的手法,为国家艺术的招牌形象带去了清新之风。“国际化”不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理念输出,而是以亲和友善的姿态融入到文字标志里:荷兰语特色的二合字母“长 ij”(long ij);以及 Rijks 和 museum 之间有意放大的视觉间隙——这些非常规的文字处理手法,令馆名及国语文化在外语人群当中更易传播。
与此相呼应的,Rijksmuseum 注重网站界面的易用性及布局弹性,尽可能降低初次使用的学习成本,减少访问设备的兼容性限制。这些本是很基础的设计思想及技术手法;但对于目标用户分布在世界各地、访问设备参差不齐的网站而言,却显得尤为重要。此外,Rijksmuseum 跳出了传统门户网站的条框,不再把首页当成零碎页面的入口汇集地,而将大部分视觉空间让位于高分辨率的图片,使得用户可以更快地接触到博物馆的实质性内容。
取而代之的,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服务的手机 app 愈渐成为网站链接的会聚入口。在这一趋势下,外部网站作为内容提供者就有必要将自身界面设计成响应式的布局,以便手持设备访问。知名科技媒体 Mashable 的创始人 Pete Cashmore 在二〇一二年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7。
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这个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撬出来,摧毁它的光韵,是这种感知的标志所在。它那“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Benjamin, 1936]8

另外,正如前文提到过的,Rijksstudio 非常看重平板电脑及触模式交互在图片浏览中的优势。平板电脑就像人见仁爱的宠物——它们被抱起、抚摸;呈现于平板电脑之上的内容与用户显得格外接近——它们如字面义般地“触手可及”。再配合上图所展示的场景——暖炉、毛毡,北欧式的家居感油然而生。这无疑为便携设备的触屏式交互体验注入了一层极富温暖的隐喻。
创作数码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或许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应该谨慎地使用“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术语。Gorgels 在论文中没有引入任何跟“后现代”相关的字眼,并小心地运用着“当代”(contemporary)一词。但是,仅仅在读到标题“创作你自己的艺术杰作”(Make Your Own Masterpiece!)之时,我便立刻想起 J.-F. Lyotard(利奥塔)对“什么是后现代”这一问题的应答——
杜尚在一九一二年与何种预先假定决裂?人们必须制作一幅画——即便是立体主义的画——的想法。而布伦又检验了他认为在杜尚的作品中安然无损的另一预先假定:作品的展示地点。[Lyotard, 1979]9

Marcel Duchamp(马塞尔·杜尚)用《Fountain》和《L.H.O.O.Q.》展示了一类创作手法,并引出了“现成品”(readymade)的概念。Gorgels 举例题到了 Mark Creegan 在 Rijksstudio 中创建的一个线上图片合集,名为“Bottom Lefts”(左下角):Creegan 从多幅线上展出的油画作品中截取局部,收录其中——它们全都是作品的左下角那一块。借助 Rijksstudio 这个 web app 的编辑、收藏、分享等功能,Creegan 不仅以现成的线上展品为基础,创作出了一件新的“抽象”作品,更完成了在线展示及传播等发表流程。
正如 Daniel Buren(丹尼尔·布伦)曾已经自己的实践所启事的那样,艺术作品的展示不再限于博物馆或画廊等专门空间。在数码复制的时代里,Creegan 完成了另一次脱离博物馆、乃至脱离实体空间的展示行动。引用 Benjamin 的话来说——
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了着眼于对可复制性艺术品的复制。[Benjamin, 1936]10
换言之,曾经的机械复制品已经是一种展示途径,而今的数码复制及互联网工具则将这种展示途径的扩大化推上了另一个台阶。“可复制性”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种属性,在 Benjamin 的语境中,无疑散发着共产主义的气息。换言之,公众化的、远离神话或宗教献祭的艺术作品,将愈来愈包含如下特质:将可复制性融入到自身内部,甚至最初就将可复制性做为自身展示的一项重要考量。
如若继续将语境延伸到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数码时代,艺术作品或许将愈来愈包含这样一种特质:适于数码复制,适于互联网传播;甚至,作品的呈现从根本上就依赖“线上展示”这种独特的技术管道。
“人人都是……”

Detail, Sistine Madonna, by Raphael. (Source: Wikipedia)
我们已经超越了奉艺术作品为神圣而对之崇拜的阶段;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较偏于理智方面的,艺术在我们心里所激发的感情需要一种更高的测验标准和从另一方面来的证实。[Hegel, 1835]11
当艺术作品失去礼仪功能而从献祭的神坛上走下,又或者当 Raphael(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受制于礼仪而从主祭坛上被撤下,它们的膜拜价值逐渐褪去,而新一轮的展示价值必须由新一轮的观众来构建——“民主”的概念提供了很好嫡出路。在数码复制的时代中,被冠以文化速食者(culture snacker)之名的群体成为目标接受者。Gorgels 很明确地将他们看作是昔日的文化观光客(culture tourist)在这个时代中的对应者。继而,“人人都是文化速食者”“艺术家就在我们中间”等口号迭起——正如“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老调以新式乐器重新奏响——“民主”的概念再一次被借用作鼓动的力量。
当然,如何将理念付诸实践也是 Rijksmuseum 一直在思考并执行的。
随着分发媒介的便利化,将内容开放给所有人、不限智慧产权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意见(communis opinio)。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运动也进一步推助了这种舆论观点。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和国会图书馆在这方面是很好的榜样;然而多数博物馆或档案馆虽占据了大量不限版权的资料,却很少开放给公众。
《WIRED》杂志前主编 Chris Anderson 曾提出“开放式内容”(open content)这一概念12,与此相结合的还有“开放式设计”(open design)13。图片不只是被发现、被收藏继而被发布;它们还应该被利用起来。用户对图片进行修改,制作出一些搞笑的效果,甚或由此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之后再分享出去。近年来,这样的实践因开放式设计运动被赋予了更大的深度。据 Anderson 所言,利用雷射切割机、印花机、3D 打印机等新技术和新设备,如今在媒体实验室甚至家中都能方便地制作出实际产品来14。
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礼仪这个母腹中的解放,其产品便增加了展示的机会。[Benjamin, 1936]15
Rijksmuseum 同时在线上和线下开展活动,邀请知名艺术家和设计师一同来使用 Rijksstudio,制作并销售周边产品;以此鼓励文化速食者、艺术爱好者乃至更为专业的艺术相关工作者参与进来。
光韵存否?又或是虚拟光韵?
光韵之争时而复燃,二〇一一年 Google Art Preject 启动时有过一次,Rijksstudio 上线时又再次发生。倘若在显示器前就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为何还要去博物馆?我以为,关于光韵的迷思 Benjamin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早已给出了相当明确的阐释——
把光韵界定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本质上远的东西就是不可接近的,不可接近性实际上就成了膜拜形象的一种主要性质。膜拜形象的实质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Benjamin, 1936]16
Rijksstudio 用“原图”提供了一种“如此贴近”的体验,然则数码复制品本质上却又将“原作”安全地保存在了一定距离之外。所以,我将 Gorgels 的论文和 Rijksmuseum 一系列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实践,看作是对 Benjamin 文本碎片的一次重新书写。

The Milkmaid, by Vermeer. (Source: Wikipedia)
Rijksmuseum 坚信,就算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原作复制品的细节,参观实体博物馆的趣味也不会损减。他们将在线浏览视作“营销工具”,Jan Vermeer(扬·弗美尔)的《倒牛奶的女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巨量复制品反而僵化了原作的光韵,刺激人们前来参观。关于原作复制品对原作的影响,Benjamin 也持有类似的乐观态度——
由于对艺术品进行复制方法的多样,便如此大规模地增加了艺术品的可展示性……现在,艺术品通过对其展示价值的绝对推重便成了一种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Benjamin, 1936]17
最后,Gorgels 以 Susan Hazan 博士的“虚拟光韵论”为论文收尾——
我们认可艺术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我们也畏惧我们尚不够了解的东西。倘若我们可以退一步与这种畏惧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对新媒体技术怀有赏鉴之心,那么我们甚至有可能洞悉到人类奋斗成果的古老光泽,以某种方式重获失去的光韵——藉虚拟之名。[Hazan, 2001]18原作依然在场
虽然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较多地落在了 Rijksmuseum 此番 web 项目的变革之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博物馆的翻新从头,依然在馆藏的实体展示及其配套空间和设施。历时十年多的主馆改建是 Rijksmuseum 投入了最多人力及物资的重点项目。如果对欧洲建筑改造嫡传统及相关法规略有耳闻,就可以想象这个改建项目开展前的决心之大以及设计和施工的任务之艰。

Asian Pavilion, Rijksmuseum. (Source: Rijksmuseum)
根据 ArchDaily 的报道19,西班牙建筑工作室 Cruz y Ortiz 对主馆的入口进行了重点设计。并且,在主馆南侧的花园中加建了独立的、二层高的亚洲馆(Asian Pavilion)——其四面环水,不规则造型的立面由灰暗的葡萄牙石灰石和玻璃构成,与主馆的红砖墙形成鲜明对比。亚洲馆专用于展示来自东南亚各国的艺术品,横揽三百六十五件藏品,纵跨上下四千年。另外,曾经因卢浮宫项目而声名鹊起的室内设计师 Jean-Michel Wilmotte 也受邀参与到本次改建之中。
随着主馆的重开,菲利普侧翼(Philips Wing)于三月转入了改建状态。
参考文献:除特别注明者,本文图片来自 MW2013。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光韵(aura)是 Benjamin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引入的术语。Aura 的汉译向来颇有争议,“光韵”这一译法参考自王才勇先生的译本,出处同上。↩Peter Gorgels, “Rijksstudio: Make Your Own Masterpiece!”, Museums and the Web, 2013.↩同 1。↩同上。↩同上。↩Pete Cashmore, “Why 2013 Is the Year of Responsive Web Design”, Mashable, 2012.↩同 1。↩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久久七年。↩同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Chris Anderson, “Free: 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 Hyperion, 2009.↩Chris Anderson, “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Crown Business, 2012.↩同上。↩同 1。↩同上。↩同上。↩Susan Hazan, “The virtual Aura — Is there space for enchantment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Museums and the Web, 2001.↩“Rijksmuseum / Cruz y Ortiz Arquitectos”, ArchDaily,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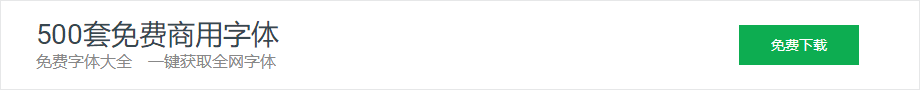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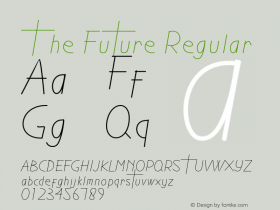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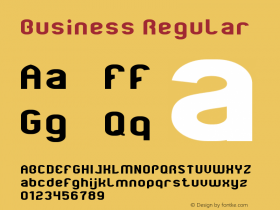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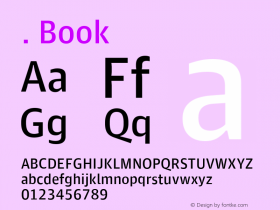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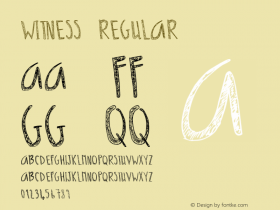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240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240号